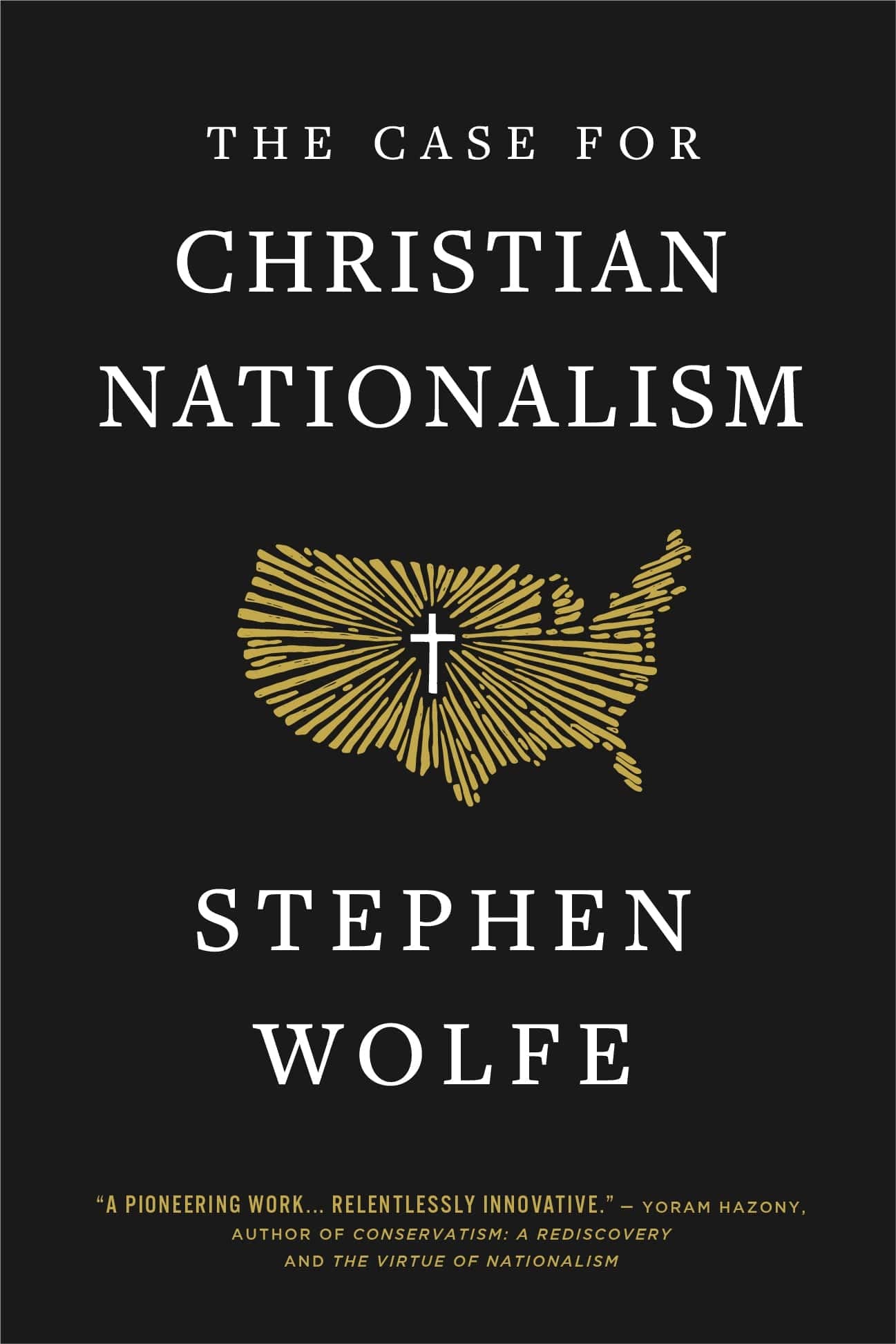 我第一次與斯蒂芬·沃爾夫(Stephen Wolfe)交鋒,是因爲讀了他的著作。當時我正在做博士研究,研究和他的領域相似的思想主題,也會讀到類似的資料。我在論文中引用了沃爾夫的文字一兩次,畢竟他擁有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博士學位,現在是「沃爾夫郡的鄉村學者」。從那時起,我就會時不時地讀到沃爾夫的文章,並在推特上看了他的一些推文。當我看到他有一本即將出版的厚重著作《支持基督教國族主義》(The Case for Christian Nationalism)時,我渴望進入對這樣一個及時和有爭議話題的嚴肅探討。
我第一次與斯蒂芬·沃爾夫(Stephen Wolfe)交鋒,是因爲讀了他的著作。當時我正在做博士研究,研究和他的領域相似的思想主題,也會讀到類似的資料。我在論文中引用了沃爾夫的文字一兩次,畢竟他擁有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博士學位,現在是「沃爾夫郡的鄉村學者」。從那時起,我就會時不時地讀到沃爾夫的文章,並在推特上看了他的一些推文。當我看到他有一本即將出版的厚重著作《支持基督教國族主義》(The Case for Christian Nationalism)時,我渴望進入對這樣一個及時和有爭議話題的嚴肅探討。
這是一篇很長的書評,所以讓我在一開始就先陳述我的結論。我理解並同情人們對類似基督教國族主義的渴望,但如果這本書代表了該主義的精華,那麼基督教國族主義就不是教會或我們國家所需要的答案。儘管沃爾夫在部分內容裡做了很好的資料整理工作,但我們必須拒絕這一整體項目。
書中的信息——種族不應該混合、異端可以被殺死、暴力革命的合理性、我們的國家需要的是一個像凱撒一樣有魅力的領袖來提高我們的意識並激發人民的意志——可能與19到20世紀的某些鐵血國家主義有相似之處,但這不是一個尊重和代表基督之名的民族主義。
讓我首先承認,人們對類似基督教國族主義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本書最精彩的部分是沃爾夫關於「文化基督教的好處」這一章節,特別是「慶祝衰退」的部分。沃爾夫正確地認爲,雖然文化基督教不能拯救罪人(也就是說,福音的信息被託付給了教會而不是公民秩序),但基督教文化在福音的方向上既可以幫助預備人心,也可以說服人接受福音(213頁)。僞善和掛名基督徒的確很危險——牧師們應該也確實警告過會眾這一危險——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否定那些將人們推向聖經真理和基本道德方向的社會文化。
太多的基督徒在不考慮其他選擇的情況下,迅速丟棄了這種文化基督教。沃爾夫問道:「但你難道不願意生活在一個社區裡,在那裡你可以信任你的鄰居,根據基督教道德標準對行爲、言論和信仰有共同期望嗎?難道你不願意擁有具有基督教文明標準的體面、尊重和受教的鄰居,即便這只是文化上的嗎?」(223頁)
這些都是好問題。我和沃爾夫一樣,對那些似乎更喜歡一個敵視基督教社會文化的基督教領袖感到困惑不解。我看到我自己的宗派中的牧師對基督徒失去權力和成爲社會少數派抱有幻想,好像君士坦丁毀了一切,只要我們能失去權力、變得更加邊緣化,我們的影響力就會大得多。
接受文化基督教帶來的代價,或者承認文化基督教允許某些罪的存活是一回事;對聖經地帶的類基督教文化說「再見」是另一回事——這是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在沃爾夫詳細引用的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所做的(224-25頁)。沃爾夫注意到摩爾是爲此歡欣鼓舞,「我們不再有梅伯里(虛構的南部社區,缺乏黑人人物和1960年代的種族緊張局勢——譯註)了,如果我們曾經有過的話」(226頁)。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可能使一些孩子保持在完整的家庭中。「但是,」摩爾總結道,「這幾乎算不上復興。」(225頁)誠然,這不是復興,但如果我們可以的話,是不是可以保留一些東西?
在過去的五年裡,我在私人場合發表過大概十幾次小型演講。我曾對我的朋友和同事說過以下這些類似的話:
我們必須認識到,人們現在對這個國家感到害怕和灰心。他們看到美國的基督教文化正迅速變得越來越淡薄,他們看到傳統道德觀——特別在性和性別議題上——不僅被扔到海裡,而且還遭到立法的阻擊。當然,我們不應該向缺乏敬畏的恐懼和驚慌讓步,我們也不應該把政治當作偶像。我們不應該像那些不敬畏神的人一樣好鬥——那是世俗的鬥爭方式。但人們希望看到他們的基督徒領袖——牧師、思想家、作家、機構負責人——都願意爲真理而戰。你可能認爲你的朋友或會眾花了太多時間看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或轉發本·夏皮羅(Ben Shapiro)的推特,或在YouTube上尋找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視頻,或閱讀道格·威爾遜(Doug Wilson)的最新著作,我與他們都有神學上的分歧(畢竟他們中有些人甚至不是基督徒),但人們被他們吸引,因爲他們對真理提出了某種充滿自信的主張。神的百姓看到世界被道德混亂所淹沒,他們希望得到幫助,進行勇敢的抵抗;但事實上他們得到的是可敬的退卻。
2022年的網上關於「溫和」的辯論是2021年關於「同理心」辯論的翻版。在這兩種辯論中,有人提出了一個觀點:「嘿,這個詞不應該代表我們基督徒見證的全部。事實上,就其本身而言,這個詞可能偷換了一些不好的想法和假設。」有許多聲音附和這一觀點。
另一些基督徒則回應說:「哇,等一下。耶穌很有同理心。我們應該彼此善待、愛我們的鄰舍。你爲什麼要反對耶穌?」這導致前述的那組人說:「這不是我們真正在談論的問題。」同時,還有一組人認爲「溫和」與「同理心」都不對,並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你不以厭惡和攻擊對手來堅持自己的觀念,那麼你就是一個被「大夏娃」俘獲的傻瓜。如此反覆之後,談話就演變成了站隊。
儘管這些討論可能令人沮喪,但它們突出了福音派情感裡的一個重要差異。我多年來一直使用「溫和」(winsome)這個詞。這是個好詞,我很樂意爲之服務的改革宗神學院(RTS)有這樣一個非官方美名:「溫和的改革宗」。如果「溫和」意味著我們以尊重和文明的態度參與思想論辯、尋求在可能的地方建立橋樑,那麼這當然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問題是,當「好客」和「同理心」不再由我們的言行定義,而是由我們的言行給人們帶來的感受來定義。基督教就成了「我是個好人」、「我不會做任何事來破壞你對我的好感」,實質上是屈服了。
另一個問題是,「溫和」幾乎總是朝一個方向發展。那些「溫和」的人常常小心翼翼地對LGBT+聽眾恭敬謙卑地說話,卻急於對MAGA人群說作出先知般的講論。許多保守基督徒已經厭倦了總是處於防守狀態,並且總是不得不以左傾世俗主義者認可的方式傳達他們的信念。他們想要的不僅僅是一個宗教自由的小島(在那裡我們保證不打擾任何人),他們想要的是對真理的有力辯護。
像基督教國族主義這樣的東西,它的吸引力在於,它提出了一個替代投降和失敗的強有力方案。很少有保守的基督徒擁有類似於複雜的政治哲學類的東西。但他們知道所謂的同性婚姻是錯誤的,變裝皇后是不好的。因此,如果政治哲學的兩個選擇是:(1)支持同性「婚姻」,因爲這是多元化的結果,並捍衛變裝皇后敘事,作爲對公民自由的祝福;或者(2)基督教國族主義;那麼這個國家的數百萬基督徒都會選擇後者。我想像同樣的基本等式也解釋了對天主教整體主義(Catholic integralism)這一新發現的興趣。
我很同情許多基督徒想要類似於基督教國族主義的原因。他們不一定是在尋找文化鬥士。他們只是不希望知道對基督教倫理越來越多的敵意都是他們想像出來的,或者真的是他們自己的錯。這些基督徒正在尋找領導力,他們在尋找信心,他們在尋找一種方法,不僅可以宣稱基督教思想有權利存在,而且基督教思想是正確的。當一本長達475頁的書,其中有數百個來自阿爾圖修斯(Althusius)和圖倫丁(Turretin)等神學家著作的引用,而且還在亞馬遜上排名前100位時,你就知道有比對政治理論的熱情更深層的東西在背後。許多基督徒想要一個替代衰落和退縮的方案。我也是如此。但基督教國族主義不是答案。
我即將開始我的書評,但首先讓我對這本書難以評論的原因做一些初步解釋。
首先,這是一本很長的書,涉及很多領域——從哲學到歷史到神學到政治理論。沃爾夫有很多話要說,我也有很多想要回應的。但寫書評不是寫書,所以書評作者必須克制自己。如果你想讀的是對這本書更充分的總結和更全面的評價,我推薦尼爾·申維(Neil Shenvi)分四篇文章寫下的評論。
第二,這是一本從個人角度所寫下的書。雖然有著大量的腳註和學術研究作爲支撐,但這本書並不必然是對公民社會本質進行的冷靜學術反思。正如沃爾夫在最後一頁最後一段中所說:「這本書不是智識操練,也不打算只是對基督教政治理論領域的一個貢獻。它是個人性的,是對未來的展望,而我的家庭是這個未來的一部分。」(478頁)
作者這樣說了之後,我們就很難知道這本書應該作爲政治理論著作、歷史文獻綜述,還是作爲個人宣言來評論。沃爾夫不僅僅是在論證建立原則或想要按照摩西律法的兩塊石板立法,他還在爲暴力革命辯護(324頁)並呼籲「偉大的復興」(435)。如果認爲沃爾夫的興趣只是在於解決古人的爭論,那就錯了。
第三,評論《支持基督教國族主義》這本書並不容易,因爲沃爾夫對自己的主張和思想的批判性參與有其前設。在書的開頭,沃爾夫強調他致力於使用「一種古老的」寫作風格,即依靠實際的論據、邏輯連貫性和學術性論證。他對如此多的基督徒「訴諸於修辭、只發推特的信條和浪費個人信用來爲不同的原則和應用做出斷言」(19-20頁)表示哀嘆,他譴責那些「攻擊那些不同意的人」和「號召共同偏見或情緒的人」。(20頁)
然而,沃爾夫在對待那些不同意他觀點的人時並沒有遵守這些自己主張的理想。他把他的對手說成是「依賴政權的福音派」(341頁),並把他們描述爲「在修辭上被沿海精英的情緒所奴役」(456頁)。同時,他預計「(對他親俄觀點)最激烈的批評者將是最喜歡(美國全球帝國主義)的基督徒。」(445頁)
正如左派預設任何反對其意識形態的人都是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和反變性的老古板一樣,右派的一些聲音也預設任何不願意朝著基督教國族主義方向前進的人都一定是賣國賊,急於討好世俗精英的邪惡陰謀。這種姿態很難鼓勵公開和真誠的思想交流。
儘管有這些困難,我還是想對《支持基督教國族主義》一書提出一些實質性的批評。我將把我關心的問題歸納在四個小標題之下:國家和民族、教會的本質、新教政治思想和前進的方向。
一、國家與民族
沃爾夫自己承認,他的定義特立獨行,而且據我估計,他對同樣事物的定義往往前後不一致。例如,在沃爾夫的思維中,「民族/國家」(nation)這個重要的概念有時好像是在說一個種族,有時更像一種文化,有時像對人和地方的熱愛,有時更像一個傳統的民族國家——有一套明確的法律、一個執政的行政長官,以及擁有刀劍的力量。這本書封面上有一張美國地圖,中間有一個十字架,所以這本書似乎是關於我們所知道的美國這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但在其他時候,很明顯沃爾夫不喜歡「民族/國家」這個概念,他對這個詞有著自己的理解——因此他將「國族主義」定義爲意識到自己的「族群」(people-group)有著自然的好處,因此要爲自己的族群服務,並使自己的族群區別於其他族群。(135頁)
沃爾夫對這個「相似性原則」(similarity principle)的辯護有很多問題。它建立在一個軟弱和基於猜測的預設上,這個預設就是:即使沒有犯罪墮落,人們也會形成不同的民族,它對人類對墮落的傾向給予了太多的信任,而且它對我們對「相似性」的渴望如何被罪所玷污考慮得太少。恩典可能會使自然的事情更加符合創造設計,但它往往是以我們感覺不自然的方式進行的。
同樣,沃爾夫的主張也沒有考慮到聖經是如何相對化了我們對家庭的觀念(可3:31-35),拆毀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弗2:11-22),並將一個多族群和多語言的現實(以及盼望的未來)看爲一種天上的美事(啓5:9-10)。
我也看不出沃爾夫所拒絕的西方普遍化傾向與沃爾夫所使用的自然神學和自然法之間有什麼矛盾(顧名思義,後者是指得到普遍接受的、導致獲得普遍肯定真理的方法)。申維的評論在民族性問題上寫得特別好,所以我不會在這裡重複所有相同的論點。
但在從這一點出發之前,值得一提的是,沃爾夫留下了一些嚴重的問題沒有回答。沃爾夫經常譴責世俗精英強加給我們的心理習慣,這種習慣使基督教國族主義者感到需要證明他們不是種族主義者、親緣主義者或排外者。沃爾夫拒絕按這些規則行事(456-57頁)。我理解這種挫折感。但是,在一本500頁的書中,沃爾夫肯定不應該錯失良機,也不會向時代精神叩頭,他應該清楚地說明他在爲什麼而爭論,沒有在爲什麼而爭論(特別是當他在VDARE.com上讚許地引用塞繆爾·弗朗西斯時)。
沃爾夫說,國族主義的特徵是,「每個民族群體都有權爲自己考慮」(118頁),「沒有一個國家(正確的概念)是由兩個或更多的種族組成的」(135頁),我們「在相似的人中過日常生活的本能是自然的,而且是天然的,它是爲了你的益處」(142頁)。以及「將一個不屬於自己的群體排除在外就是承認人的普遍益處」(145),「屬靈上的合一對正式的、教會間的合一來說是不足夠的」(200頁),以及「一群人成功追求完整利益的最合適條件是文化上的相似」。(201頁)
我們該如何對待這些論點呢?沃爾夫的主要關注點是民族國家的移民政策嗎?這就是他對一個民族的自我毀滅提出警告?(171頁)他是否在論證我們不必爲愛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地方多於其他家庭、國家和地方而感到羞恥?這也是他關注的一部分,聽起來也合理。
但是,你不必是一個左翼人士也會想知道這些「相似性」論點在實踐中如何實現。在一個腳註中,沃爾夫拒絕了現代種族主義原則,並否認他在提出「白人國族主義」論點(119頁),但如果我們不能接受國家圍繞意識形態建立的觀念,而是把各個國家按文化相似性去建立,那麼黑人和白人(更不用說亞洲人、西班牙人和美國原住民)會有多少合作和合一,或者他們是否應該嘗試一起生活和敬拜,這都成了公開的問題。
還有,這真的是福音所要推動的方向嗎?我們真的要在地球上追求一種與天堂中的社會秩序如此不同的社會秩序嗎?我們真的那麼肯定我們對像我們這樣的人的愛和對不像我們的人的排斥是上帝賜予的傾向,而不是墮落的傾向嗎?
如果這本書沒有其他問題,沃爾夫對變得「更加排外和注重種族」(459頁)的大力辯護應該讓所有準備追隨沃爾夫國家復興願景的人停下腳步。左派認爲種族主義無處不在的事實,並不意味著種族主義真的無處不在。沃爾夫可能摒棄了當代的種族主義定義,但他沒有明確說明他關於親緣關係的想法與過去的種族主義思想有什麼不同,後者同樣被用來禁止異族通婚,並認爲強制執行「分開但平等」的法律沒有什麼不公之處。
因著神的恩典,美國在過去60年裡在解決種族主義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我看不出沃爾夫的設想如何不是在錯誤的方向上邁出了一大步。
二、教會的本質
沃爾夫政治理論的關鍵是,「一個基督教國家是一個以特定的生活方式存在於塵世,以反映在基督裡天國樣式的國家」(174頁)。我將在下一節中詳細介紹新教的政治思想。我目前的批評不是關於道德哲學,而是關於系統神學。
值得稱道的是,沃爾夫清楚地區分了公民的領域和教會的領域。他堅持一種(類似的)兩國論神學。沃爾夫的主張並不意味著神權政治(theocracy),也不是神治主義(theonomy)。「基督教國家不是基督屬靈的國度,也不是末世的實現;它並非建立在恩典或福音的原則之上。」(186頁)然而,民事政府應該把人們引向基督教,因爲「當一個地上的政權把人民引向天國時,它就是一個基督的王國。」(195頁)
沃爾夫並沒有把教會和世界混爲一談,但他認爲「基督教國家是今生彰顯永恆生命的整全體現」。沃爾夫反對(浸信會)將教會作爲天國「大使館」或「前哨站」的主張(222頁)。教會可以給我們天堂生活的「主要樣式」(藉著公共敬拜),但只有基督教國家才能給我們天堂生活的「完整樣式」。因爲除了敬拜,基督徒還需要服從於民事長官,並構成了一個民族,「其文化習俗和自我認知提供了天堂的預示」(223頁)。簡而言之,沃爾夫認爲,一個基督教國家應該順服基督的安排「使地上的城市成爲天上城市的類似物」(209頁)。
我不同意這個結論。這暗示了公民社會可能與天上的樣式相似。說在未來的生活中我們將更深入地享受今生的一切美好,這是一回事;暗示天上國度的類似物可以在地上的城市中找到是另一回事。與沃爾夫相反,我認爲教會才是天上之城的「前哨」、「大使館」或「殖民地」。
這與救贖歷史的全貌吻合。天國的樣式首先出現在伊甸園;然後在以色列找到對伊甸園的某種反映(神同住的土地,用伊甸園的語言描述,以伊甸園的邊界爲標誌)。目前,神住在教會中與祂的子民在一起(在那裡,以色列的司法處罰被重設爲教會的除名懲戒,伊甸園的富足景象通過慷慨賜下恩典供應我們的兄弟姐妹而得到體現);最後,在末後的日子,這個世界的國度將成爲我們主和祂的基督國度(啓11:15)。
只有在這個時代結束時,我們才能期待天國降臨到地上。在目前,天國的相似物居住在教會裡。沃爾夫引用馬太·亨利的話說,「凡是在這個世界上優秀而有價值的東西」都將進入新耶路撒冷(222頁)。但亨利在關於啓示錄21:9-27的同一段註釋中,並沒有把地上之城看爲天上新耶路撒冷的實現。馬太·亨利認爲,新耶路撒冷是「上帝的教會在其榮耀、完美、勝利的狀態下」的寫照(《馬太·亨利聖經註釋》)。
畢竟,新耶路撒冷是新婦、羔羊的妻子、教會的願景(啓21:9)。當希伯來書將教會描述爲「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和「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來12:22-23)時,我們很難說教會不是天國樣式的某種不完整形像。
基督在這個時代的主要關注點是教會。雖然許多機構對塵世生活和人類的繁榮做出了貢獻,但耶穌並沒有承諾要建立教會之外的任何機構(太16:18)。從《支持基督教國族主義》中得到的印象是,教會只是在一個更大的項目中發揮支持性的屬靈作用,而這個項目涉及到的是公民社會的秩序,使人們完全受益。沃爾夫的願景是以國家爲中心,而不是以教會爲中心。
例如,如果我們要經歷偉大的復興,我們必須希望並祈禱有一個如神一樣的行政長官,「人民視其爲國家的父親或保護者,……一個有尊嚴和偉大靈魂的人,他將帶領人民走向自由、美德和神性,走向偉大」。(279)書中沒有多少關於禱告的內容,這本身好像並不重要,對禱告的最強烈(唯一的?)勸告是,我們應該求神興起一個「基督徒王子」——一個「能夠鎮壓上帝的敵人並使神的百姓得到高升、神百姓的敬拜得到恢復,男性在地上的突出地位和統治精神得到恢復的王子;一個肯定並保護上帝的百姓和土地,不允許他們被擊敗或被佔領;並激發對自己基督教國家的熱愛的領導人。」沃爾夫在這一章的結尾敦促讀者「禱告求神通過一位基督教王子帶來偉大的復興」(322頁)。
除了質疑盼望「一個有分寸的神權凱撒主義」和「我們時代的世界震動者」(279頁)是否有智慧之外,我看不出這如何一直是,更不用說應該是上帝子民的偉大盼望。我同意沃爾夫的觀點,即教會不應成爲政治活動的中心,但我們真的要堅持認爲行政官有權力「解決教義衝突」,調節宗教會議,並「確認或否定他們的神學判斷」嗎?當行政官對教會的教義「保留其超越權柄」時(313頁),就我們的經驗而言,我們能看到教會變得更好嗎?
在沃爾夫的願景中,牧師「更像軍牧」(470頁),他希望上帝的子民自願結社,「沒有牧師的領導」(471頁)。犧牲教會的重要性來增加國家重要性的基督教國族主義會讓我們付出極其高昂的可怕代價。
三、新教政治思想
沃爾夫對早期新教政治思想的綜述和運用值得稱讚,不應遭到輕易否定,但沒有一種新教(或改革宗)的政治神學能夠成爲任何地方、任何時空、任何國家的金科玉律。讓我通過提出三點來支持我的這個結論。
第一,沃爾夫對16和17世紀的資料中進行的文獻綜述結論基本正確。
在正統宗教改革進行的早期和高潮時期,大多數神學家都相信民事官員有權召集和舉行宗教會議,有必要執行摩西十誡的兩塊法版,並相信國教原則(established principle,即國教得到政府財政支持並享有某些法律特權)。他們認爲,民事官員有權審判異端、強制執行某種教義和敬拜規範,並使用死刑(在極端情況下)來保護社會免受罪惡和錯誤教導的影響。
離開天主教之後,新教神學家們堅持所謂的良心自由。正如沃爾夫指出的那樣,他們教導說,信仰是一個內在的、被一種觀念說服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行政長官不能使用國家的行政強制力來鎮壓錯誤的信仰(353頁)。
這些舊觀點的反對者應該注意不要誇大其詞。在我們這個時代,以審慎的態度來反對例如「褻瀆法」的可執行性是一回事,論證這種法律在原則上是錯誤的則是另一回事。沃爾夫值得稱讚,因爲他有勇氣如此相信,並提出自己的觀點迫使基督徒們更仔細地思考大多數西方基督徒認爲不可能的一系列結論。
第二,儘管沃爾夫的理由可能很有啓發,但它絕不構成新教的立場。
如果古老的觀點就是經典,那我也無話可說。但新教的公共神學在圖倫丁去世後仍在不斷發展,我們也不應該認爲1700年後的一切都可以算爲「啓蒙運動」的結果。到17世紀末,新教的神學家、倫理學家和自然法思想家開始重新思考強制宗教信仰一致性是否可行,並質疑地方政府在宗教事務中擁有崇高權力是否真的出於聖經。
例如,塞繆爾·馮·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在1687年的作品《就公民社會而言的宗教性質和資格》(Of the Nature and Qualification of Religion in Reference to Civil Society)中認爲,國家不是爲宗教而建立的,宗教作爲人類自然自由的一部分,不能委託給執政者治理。普芬道夫認爲,民事官員的主要職責不是對轄下的社會進行屬靈的管理,而是確保百姓的安全和保障——這才是建立民事政府的目的。
可以肯定的是,普芬道夫並沒有主張取消國教,他也不認爲君主必須容忍每一種不同的信仰流派,但他的確把新教世界推向了宗教寬容的方向,並提出了君主不應強制執行除了自然宗教原則之外任何宗教信仰的理由。當然,你可以不同意普芬道夫的觀點,但他是一個正統的路德宗基督徒,他的觀點建立在數百處聖經經文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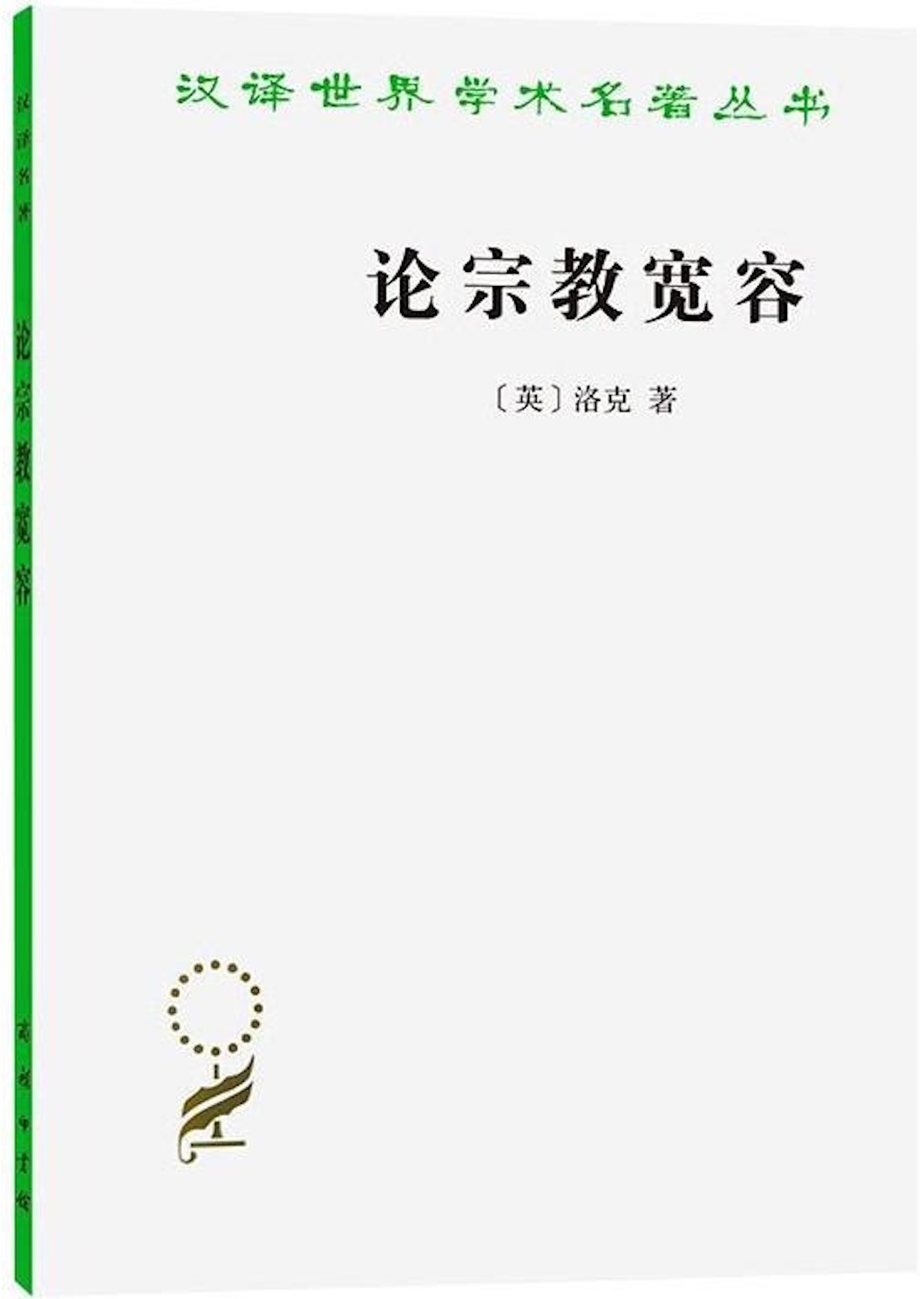 普芬道夫遠不是唯一一個在這個方向上發展的思想家。1689年,約翰·洛克(John Locke)在其著名的《論宗教寬容》(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1689)中認爲,民事官員應該容忍虛假的宗教。「如果有一個教會是拜偶像的,民事官員是否也要容忍呢?」洛克提出了這一設問。他的回答後來被證明很有影響力:「如果我們賦予地方民事官員權力鎮壓偶像崇拜的教會,那麼同樣的權力在另一個時間、另一個地點就會被用來毀掉一個正統的教會。」
普芬道夫遠不是唯一一個在這個方向上發展的思想家。1689年,約翰·洛克(John Locke)在其著名的《論宗教寬容》(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1689)中認爲,民事官員應該容忍虛假的宗教。「如果有一個教會是拜偶像的,民事官員是否也要容忍呢?」洛克提出了這一設問。他的回答後來被證明很有影響力:「如果我們賦予地方民事官員權力鎮壓偶像崇拜的教會,那麼同樣的權力在另一個時間、另一個地點就會被用來毀掉一個正統的教會。」
普芬道夫和洛克都是針對《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 1685)的撤銷而寫下這些文字的,該敕令要求法國胡格諾派教徒皈依天主教,否則將面臨終身監禁,或不得不逃離該國。與其讓君主對教會的教義和崇拜擁有最終決定權,寬容看起來更好,更有利於實現基督信仰的目標。擺脫嚴格執行宗教國族主義的做法不是由自由思想家和無神論者,而是由堅定的新教基督徒推動的。
1697年被絞死的20歲學生托馬斯·艾肯海德(Thomas Aikenhead)是英國最後一個因褻瀆罪遭到處決的人,這是因爲越來越多的新教基督徒相信有一種更好的方式可以讓不同宗教的人群共存。在這本書的開頭,沃爾夫提出了他的一個原則:「我的觀點既非來自歷史上宗教國族主義的實例,也不想浪費時間去否定『法西斯國族主義』。」(26頁)考慮到該書的目的是要對現實說話,如果沃爾夫能說明他的基督教國族主義版本在哪裡得到了實施,以及它是否被證明成功地促進了類似天國的地上社會,那就更好了。但我們從來沒有看到沃爾夫的願景付諸實踐,難道沃爾夫希望我們像過去接受社會主義一樣,從未真正實驗過就接受基督教國族主義嗎?
雖然美國有很多缺點,雖然美國基督徒面臨很多問題,但你很難找到一個正統新教徒掌握更多政治權力、擁有更多文化影響力,並且有更多自由按照自己的良心實踐信仰的國家。
我總體上同意亞倫·雷恩的「消極負面」社會理論。我認爲我們正處在一個深刻的文化變革的時刻,反對正統基督信仰的力量很多,也很強大。哪些基督教機構和個人會保持忠心還有待觀察,基督教世界的分裂正在進行中。
然而,從體制和文化上來說,美國對符合聖經的基督信仰的支持仍然多於世界上幾乎任何其他國家。這的確正在發生變化,我們不應該爲這種衰落感到高興。但我敢說,這個國家的基督教——沒有國教、沒有基督教政治領袖、沒有統一的敬拜和教義——已經過得很好了。在談論塵世現實時,問一個問題「與什麼時候比?」總是有幫助的。如果說美國的實驗是失敗的,我想知道在過去的250年裡,哪個國家的基督教是成功的?
第三,沃爾夫爲支持其基督教國族主義而對美國建國的處理並不具有說服力。
在後記前的最後一章,沃爾夫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的政治傳統是否允許基督教對政治的理解、基督教政府和設立國教?」(398頁)他在這一章的結尾總結說,美國國父們「都認爲,一群有宗教信仰的百姓對於公民道德、公共幸福和有效的政府是必要的,而且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都認爲基督教在這方面提供了一些獨特的東西。」(430頁)沃爾夫說,國父們還認爲,政府在支持真宗教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可以鎮壓違反自然宗教理念的行爲。這都是事實。美國的建國之初比今天嚴格的「政教分立之牆」倡導者認爲的更加偏向基督教。
但這些結論與本書的其他部分之間存在著脫節。沃爾夫的書並沒有就基督教是公共美德所必需的,或者基督教應該在美國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擁有特權地位進行論證。沃爾夫主張的是「神權凱撒主義」(「theocratic Caesarism」),主張建立國教,主張由基督教政治領袖懲罰假教師並規範宗教的外部行爲——包括認證宗教從業人員、規範崇拜儀式和教會教義(356-57頁)。這不是美國建國的目的,而且在許多方面,這正是我們的國父們想要避免的。
正如我以前寫過的,如果說建國有一個焦點,那這個焦點就是「自由」——不是表現型個人主義的「自由」,而是對自由的承諾,即相信政府的存在是爲了保護個人權利、政府應該受到限制,政府的權力應該受到制衡。沃爾夫說,「我們的時代需要一個能夠運用正式民事權力產生巨大影響的人,並通過魅力、威嚴和個性來塑造公共想像力」(31頁)——這正是我們的憲法制度所要反對的那種蠱惑人心的本能。
在沃爾夫對建國敘事的複述中,人們相信建國時代的政治哲學與100或200年前的新教徒所相信的沒有什麼不同。例如,沃爾夫的結論是,約翰·威瑟斯彭(John Witherspoon)「對政府在宗教中發揮作用的看法與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的沒有什麼不同。」(417頁)。這遠非事實。
首先,威瑟斯彭在普林斯頓教授了一門道德哲學課程(沃爾夫多次引用了該課程的講義)。威瑟斯彭是由普芬道夫和赫奇遜以及整個新教自然法倫理學的傳統所塑造的。(在格拉斯哥有這樣一句話:那裡的學生必須忍受這樣的一個課堂:「他們的頭顱被敲打/格羅秀斯、普芬道夫和洛克」)。
另一方面,馬瑟則嘲笑道德哲學這一學科是「把一切簡化到系統中。」威瑟斯彭和馬瑟有許多共同認信的教義,但他們對教會與政府的關係則看法迥異。
作爲新澤西殖民地議會成員,威瑟斯龐和其他代表(包括其他著名的長老會牧師們)捍衛宗教自由,反對設立國教。他們共同制定的州憲法第十八條規定如下:
在本殖民地內,任何人不得被剝奪以符合自己良心的方式敬拜全能上帝這一不可估量的特權;也不得以任何藉口被強迫參加任何違背自己信仰和良心判斷的禮拜。本殖民地內的任何人不得被迫爲建造或修繕任何一座或多座教堂、一個或多個禮拜場所,或爲維持任何一個或多個牧師而支付財產、稅收或任何其他費用,特別如果這與他認爲正確的、或已經自願參與的信仰相悖的話。
可以肯定的是,新澤西在1776年所做的事情要再過50年才能在北美其他殖民地扎根。我的論點並不是說在建國時期國教不存在,也不是說存在國教是個錯誤。我的論點是,許多正統的基督徒反對設立國教,並基於歷史、審慎和出自聖經的理由反對它們。
沃爾夫知道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威瑟斯彭在普林斯頓的學生)拒絕賦予民事官員對宗教的權力,他不厭其煩地證明麥迪遜的觀點是「極端的」,他「在建國時代對宗教自由的重要性被誇大了」(423)。也許吧,但如果麥迪遜的觀點沒有那麼重要,那是因爲當時長老會和浸信會的觀點更重要。麥迪遜著名的《反對宗教徵稅評估的請願抗議書》(Memorial and Remonstrance)是爲了反對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對財產所有者徵稅以資助所有新教牧師的計劃而寫的。麥迪遜的這一文件在弗吉尼亞議會上獲得了1552個簽名。
然而,反對亨利提案的最受歡迎請願書是由長老會、浸信會和其他持異議者提交的。他們的提案提出了許多與麥迪遜提案相同的論點,獲得了4899個簽名。這些持不同意見的人知道,一個泛新教的建制國教從來沒有成功過(甚至沒有人嘗試過)。建國總是意味著以犧牲一個宗派的利益爲代價,使另一個宗派享有特權,這就是爲什麼在宗教多元化的州,取消國教的速度最快,而在一個教派占主導地位的州,取消國教的速度最慢。
今天的美國有3.3億人口,新教基督徒中包括了大量的五旬節派和靈恩派,還有黑人傳統和自由派傳統,以及數百個在無數不同事情上意見不一致的宗派,花時間夢想在美國建立一個泛新教的跨宗派「國教」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爲此,我們應該心存感恩。
讓我最後評論一下長老會,因爲我是長老會成員,沃爾夫也是。無論好壞(我會說是更好),長老會對教會與國家關係的看法是到了美國發生變化的。從1787年的重組計劃(reorganization plan)到1789年的第一次總會會議(GA),威瑟斯龐在建立一個全國性長老會上發揮了關鍵作用,當教會憲章最終獲得通過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美國版本已經獲得修改,在教會和政府之間建立了更多距離。美洲長老會(PCA)和正信長老會(OPC)使用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版本包含了那些1789年作出的修訂,限制了民事官員對宗教事務的權力。
此外,這些修改並不是起源於1780年代。1729年費城長老會通過的《修改法案》(Adopting Act)已經允許英國版本《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20章和第23章對牧師沒有約束力,牧師們不需要「接受」這些條款的含義,即認爲民事官員在中會(synods)行使教牧權柄上有控制權。除了少數例外,這個國家的長老會從來沒有主張過傳統改革宗關於民事官員的「經典」立場。
四、如何前行
這篇書評已經太長了,但還有最後一點要說明:這本書儘管在神學和哲學方面做了嚴肅的文獻研究,但在你讀完後記之後,就很難認真對待了。如果沒有後記,這本書仍然會引起強烈的反應,但人們可以說,沃爾夫設想的核心是回到16和17世紀西歐的政治秩序。我不認爲這是正確的願景,但值得考慮的是,爲什麼我們的許多神學前輩對如何管理他們的社會有如此不同的想法。從這些早期的神學家身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即便我們認爲沒有必要在我們自己的時代實施他們的政治理念。
但後記給了整本書不同的感覺。沃爾夫的後記聲稱要回答「現在怎麼辦?」的問題——但這一章由一連串鬆散的話題組成,可以公平地描述爲由38部分組成的咆哮。幾個例子足以證明這一結論。
關於進步的問題(436頁):
進步主義每一步的都在勝過你。問問自己,「每一個進步事件都有什麼樣的共同惡棍?」答案顯而易見:白人直男。那是新美國的主要外圍群體,是倒退和壓迫的化身。
關於生活在女性權之下(448頁):
我們生活在一個婦權政治之下——由婦女統治。表面來看可能並不明顯,因爲男人仍然掌管著許多事情。但美國的統治美德是女性這一惡習,與某些女性美德有關,如同情心、公平和平等。
關於女權主義的諸多問題(451頁):
你是少數民族,有怨氣嗎?向白人婦女表示不滿,甚至把你的痛苦歸咎於她們,婦女就會給你錢和派發禮物。還可以考慮兒童變性,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過度同情和有時瘋狂的母親促成的。我們現代社會最瘋狂和最具破壞性的社會學趨勢是由女性驅動的。女權主義是自我毀滅的,滋生了社會混亂。
關於女性和證書主義(453頁):
隨著學術機構迎合越來越多的女性並使其畢業,證書主義(credentialism)正在上升。這就是爲什麼女性將她們獲得的證書——「博士」或「醫生」、「教授」,甚至是「神學碩士」……放在她們的社交媒體頭銜中。
關於統治階級(456頁):
這裡沒有強有力的共同點。我們無法與他們建立起可信度。不可避免地,我們是對他們政權的威脅。基督教國族主義是對世俗主義政權的生存威脅。他們是教會的敵人,因此也是人類的敵人。
關於抵制現代生活的必要性(461頁):
我不會告訴你在這方面要走多遠,但這對你和你的家人都有好處,它爲更好的未來做了準備。我預計,大多數堅定的基督教國族主義者將是農民、自耕農和牧場主。
關於選擇職業(464頁):
我現在(對我的孩子們)說:「找到一個能使你最大限度地擺脫世俗主義統治力量的職業。」。如果你是一個白人、異性戀、認同生理性別的男性,那麼這個世界就不會給你任何好處。事實上,你的職業發展取決於犧牲你的自尊,對統治你卻不如你的人進行讚美和獻媚。即使是首席執行官,到頭來也是被「覺醒」的批評者所支配。
關於低睾丸素的尷尬(469-70頁):
基督教國族主義應該有一種強烈而樸素的美學。當我看到最近一次PCA大會的與會者穿著皺巴巴的短袖、豐滿地坐在座位上時,我感到很沮喪。我們必須做得更好。追求你的潛力:擼鐵、正確飲食、減掉父親般的身材。我們不一定都要成爲健美運動員,但我們應該成爲有力量和耐力的人。在現代營養學的控制下,以這種鬆弛的審美眼光,我們無法實現我們的目標。要對這種審美眼光嗤之以鼻,我完全期待這種情況發生,不要應付。恩典不會破壞T水平,恩典不會使睾丸激素完美地變成雌性激素。如果我們的對手想成爲胖子,想擁有低睾丸素,想喝植物油,就讓他們去吧。我們不該這樣。
沃爾夫認爲這一切令人擔憂,但他把它寫下來更令人不安。他和他的編輯們認爲用一連串的謾罵來結束這本書是個好主意,這令人費解。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尋找的文明答案嗎?離開電網生活,抱怨女人,抱怨執政者,抱怨作爲一個白人男性有多難,警告全球主義者,呼籲植物油的危險性,並責備有父親般身材的長老會弟兄們?
除了販賣關於美國帝國全球主義、女權主義全面控制之類未經證實的主張外,沃爾夫的世界末日願景——所有對世俗精英的謾罵——都引自互聯網上的左派論調。他不僅將壓迫的性質重新定義爲心理壓迫(使其更容易證明採取極端措施的合理性,更難論證事情並不像看起來那麼糟糕),他還通過提醒他們是受害者來集結自己的「軍隊」(象徵性的,但也許也是字面上的)。「這個世界是來抓你的,這個社會都恨惡我們」,這不是一個最終能幫助白人男子或任何其他認爲自己是受壓迫群體的信息。
當沃爾夫諷刺地感謝那些「將許多人從教條式沉睡中喚醒」的人,並爲「每天都有更多人覺醒」而歡欣鼓舞時,人們不難看出他的基督教國族主義實質上是一種右翼覺醒主義。如果我們沒有被壓迫無處不在、必須採取極端措施、必須推翻政權的「現實」所喚醒,那麼「覺醒」意味著什麼?
批判性種族理論告訴我們,美國已經失敗了,現有的秩序不可救藥,西方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錯誤,目前的制度是針對我們這個群體的,我們應該使種族意識更加重要。在我看來,沃爾夫的項目無非是這些相同衝動的右翼版本而已。
那麼,對於我們的國家和文明正在面臨的崩塌,我的答案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應該記住有比國家和文明崩潰更大的問題,比如罪、老我和魔鬼,比如死亡和地獄(太10:28)。作爲一個牧師,我更關注教會的和平和聖潔。當然,這些圍繞基督教國族主義的討論是在它從未像現在這樣受到注意的時候進行的,這很有意義。
一方面,這很有意義。我們正在抓緊時間尋找一些替代激進進步主義的理念。然而,考慮到目前還沒有在火星上建立新教或長老會殖民地的計劃,我們應該寬鬆而仁慈地堅持我們的政治藍圖——那些沒有可能實現的藍圖。我擔心這次討論的實際社會果效會非常小,但在教會中造成分裂的可能性會很大。
但是,如果我們必須對國家復興的策略說些什麼,那就是多方面的,而且相當普通。我們需要信心、勇氣和基督精神。我們需要忠心的教會、福音的傳講和禱告。我們應該爲信仰而爭辯。我們應該對我們的教會進行門訓,教導我們的孩子。我們應該創建新的和管理好現有的公民、教育和教會。我們應該愛我們的鄰居、分享我們的信仰。我們應該在公共場合宣傳自然和啓示性宗教的真理,並參與到政治進程中。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大多數人應該結婚生子(越多越好)。
我們的「戰略」不是一件事,它是許多事。它是培養審慎、公正、智慧和節制的美德(並理解每種美德如何需要其他三種美德)。它是建立橋樑和建造邊界。它是說出真理和給人恩典。它是努力在聖靈所結的每一個果子上成長,求神賜給我們每一種恩典的美德。它是作爲上帝之城的另一種文化模式,它是試圖在人類之城中成爲鹽和光。
我同樣感嘆美國的基督徒比以前少得多。我想讓基督徒參與爭戰,而不僅僅是妥協於投降的條件。我希望基督徒和基督徒的思想能夠對我們的國家產生良好的影響。我爲基督和他的國度的到來禱告,我希望有敬虔和智慧的民事官員,我也希望看到性別革命的失敗。
我愛我的國家,希望看到它產生更多的基督徒——主要是通過重生,但也通過來自文化基督教的益處。我們應該爲這一切禱告和努力。我只是不認爲這等同於這本書提供給我們的基督教國族主義。
我知道有一種直覺,認爲任何看起來最「保守」的立場一定是正確的,特別如果這個立場被左派所憎惡的話。但這種本能的結論並非萬無一失。而且,沃爾夫明確表示,他的主張不是「保守」的。我們最好把沃爾夫的設想看作是在激進的右派中正在增長的幾種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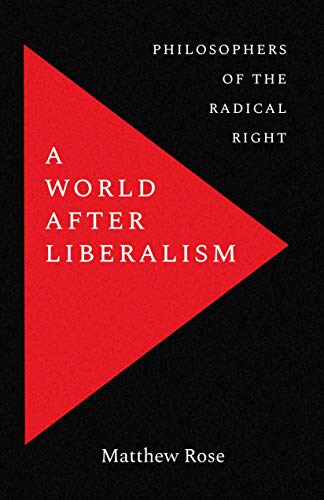 閱讀馬修·羅斯(Matthew Rose)出版於2021年的《自由主義之後的世界》(A World After Liberalism)中關於「國族主義者」的章節,你會發現許多來自塞繆爾·弗朗西斯思想的核心:保守主義運動的無能,需要激起美國中部的不滿,呼籲獨特的種族(意即「白人」)停止自我傷害並捍衛自己的國家,堅持認爲美國已經死亡、革命是必要的,以及鼓勵利用凱撒主義和一個有魅力的領導人所激發的群眾忠誠,這些都存在於沃爾夫自己的視野中。
閱讀馬修·羅斯(Matthew Rose)出版於2021年的《自由主義之後的世界》(A World After Liberalism)中關於「國族主義者」的章節,你會發現許多來自塞繆爾·弗朗西斯思想的核心:保守主義運動的無能,需要激起美國中部的不滿,呼籲獨特的種族(意即「白人」)停止自我傷害並捍衛自己的國家,堅持認爲美國已經死亡、革命是必要的,以及鼓勵利用凱撒主義和一個有魅力的領導人所激發的群眾忠誠,這些都存在於沃爾夫自己的視野中。
出自聖經的本能比出自國族主義的本能要好,基督教國族主義未能通過聖經的嗅覺測試。全身心投入這本書的人——對每一個咆哮都說「是」的人,感到受種族隔離願景吸引的人,只是在等待時機,直到基督教「王子」到來,革命就會開始的人——會在信心、盼望和愛中成長嗎(林前13:13)?他是否會因爲參與了基督的苦難而感到喜樂(彼得前書4:13)?如果萬物的結局就在眼前,他是否會爲了禱告的緣故而謹慎自守(彼前4:7)?還是說這本書在幫助我們以怨報怨(彼前2:23)?
我們不是第一個生活在艱難時期的基督徒;世界各地的大多數基督徒,以及歷史上數以百萬計的基督徒,可能會用他們的環境來與我們的處境交換。我們正在經歷的文化動盪將是一種神護理之下的恩典,如果它能引導我們更仔細地思考公民社會,更有說服力地爭奪真理,更充分地將自己交託給耶穌和他的教會,並在聖潔中成長,否則無人能見主(來12:14)。
當然,讓我們爲大復興禱告,但我們也要記住,在我們的世界和我們的土地上,我們最需要的復興是恢復真正的教義,規正我們的生活,以及復興那神聖和超自然的光,讓它在我們心中閃耀,讓我們看到上帝在基督臉上的榮耀(林後4:6)。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Rise of Right-Wing Woke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