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就像C. S.路易斯(C. S. Lewis)所建議的那樣,我們要幫助我們的讀者「讓這幾個世紀以來乾淨的海風吹過我們的心」(出自On the Incarnation: Saint Athanasius with an introduction——譯註)。也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只有通過閱讀經典」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我們接下來要審視一些可能被遺忘、但是依然和現今的教會相關,並且能幫助今日基督徒的經典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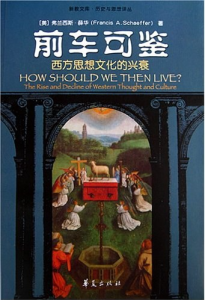 1976年,許多美國人開始意識到福音派不僅仍然存在,而且繼續在基督教世界裡活躍地發揮著影響力。當時福音派世界那些極具影響力的領袖們似乎開始用越來越充滿盼望的眼光看待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1960年代思潮帶來的充滿緊迫感的文化危機似乎已經陷入衰退。
1976年,許多美國人開始意識到福音派不僅仍然存在,而且繼續在基督教世界裡活躍地發揮著影響力。當時福音派世界那些極具影響力的領袖們似乎開始用越來越充滿盼望的眼光看待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1960年代思潮帶來的充滿緊迫感的文化危機似乎已經陷入衰退。
正如我們現在所知,事實卻絕非如此。1973年,最高法院作出了「羅訴韋德案」的最終裁決,這給全美國都帶來了影響,按需墮胎變得合法。思想界所發生的大事都爲文化變遷設定了舞台,福音派基督徒們帶著「我找到了答案」("I Found It")的胸針並建立了巨型教會,但與此同時,文化正在向著敵對基督教的世俗主義轉變,而這在一代人的時間裡不會完全顯現出來。
不過,有些人還是預見到了世俗主義文化的到來。1976年的我剛剛17歲,正面臨著高中的最後一年,並試圖理解我周圍的世界。那時,一場護教學危機已經困擾了我幾年,我需要幫助。我已經看到了很多問題和疑問,而這些問題和疑問必將在未來幾十年內爆發在美國社會的舞台上。
值得慶幸的是,我確實得到了幫助,而且是來自多方面的幫助。D.詹姆斯·肯尼迪(D. James Kennedy)向我介紹了薛華(Francis Schaeffer)的著作。於是我讀了《太初有道》(He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理性的規避》(Escape from Reason)和《永存的神》(The God Who Is There)。薛華的著作是對我的一種神學拯救。我並沒有完全理解他在書中寫下的所有內容,但我確實明白了他的主要觀點,它們給了我一種理解基督教信仰如何聯繫周圍的世界和如何回答這個世界所提出那些回答問題的方法。
當時的我在問一些非常宏大的問題,而與此同時,當時的我被一個世界所吸引,兩部英國電視系列片向我敞開了那個世界的大門,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在電視上看到過這樣的系列片。一部是由肯尼斯·克拉克男爵編劇、宏偉磅礴的《文明的軌跡》(Civilisation),我一分鐘都沒有錯過;另一部是雅各布·布羅諾斯基帶來的《人類的攀升》(The Ascent of Man)。布羅諾斯基講述的人類故事和現代科學的興起令人著迷,但我知道他所展示的很多東西與基督信仰完全相悖。
另一方面,《文明的軌跡》不太會引起這樣的警覺。當克拉克講述西方文明的故事,並以他對繪畫、建築、文學和音樂的精湛解釋來說明每一個時代時,我對每一個字和每一個畫面都很感興趣。我被迷住了,我想去看看克拉克爵士在電視上向我展示的大教堂、修道院、博物館和圖書館,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些。
但其實克拉克也在講一個故事——一個以藝術和美學價值爲中心的故事。我知道新教改革,但我還不了解克拉克男爵是在用人文主義的世界觀講述西方文明的故事。
1976年,薛華的著作《前車可鑑:西方思想文化的興衰》(How Should We Then Liv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Thought and Culture)出版了。我買到的是第一批印刷的書籍中的第一本。我從頭到尾讀了一遍,讀得很投入,因爲我知道薛華也在講述西方文明的故事。
《前車可鑑》既是一本書,也好像是一個多集的電視系列片,就像克拉克的《文明的軌跡》一樣。這不是巧合。薛華在這本書中同時刻意回答了布羅諾斯基和克拉克對基督信仰發出的挑戰,不過他對克拉克的回應最直接。但薛華是通過講述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達成這一目的的。
這本書的副標題——《西方思想文化的興衰》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這與克拉克爵士的敘事幾乎完全相反。薛華並不是不同意克拉克《文明的軌跡》中每一個論點,但他確實不同意克拉克的許多論點,更重要的是薛華不同意克拉克對人類文明敘事的人文主義詮釋。
這本書的英文題目("How Should We Then Live?",直譯爲「我們應該如何生活呢?」——譯註)讓我覺得很奇怪,直到現在仍然覺得奇怪。從英文語法上來說,它沒什麼錯誤,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奇怪的提問方式。不過話說回來,薛華這個人也很奇怪,他出了名的穿搭方式看起來就好像是上個世紀從瑞士山裡來的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確實如此。薛華和他的妻子艾蒂斯(Edith)在瑞士山區創立並指導了避難所團契(the L'Abri Fellowship),這個事工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主要是美國)各種心懷不滿和滿心困惑的年輕人,向他們介紹基督的福音。奇怪而奇妙的是,薛華採用了理性的方式,借助基督教護教學所捍衛的聖經真理來回答他們的問題。當其他領袖們在忙於建立福音派帝國的時候,薛華夫婦卻在接待數十名長髮飄飄、智力超群的年輕人,與他們的思想交鋒,同時致力於詮釋他們的文化。
 我在高三的第一週,從頭到尾讀了《前車可鑑》。根據我13歲時開始記的讀書記錄,這是我用自己的錢買的第80本書。價格是12.95美元,當時看來是花了不少錢。我知道它值這個價,但薛華的書一開始讓我感到困擾。誰的西方文明主線敘事是對的?薛華還是克拉克爵士?當我第一次讀這本書的時候,我並不確定。克拉克爵士指出,幾百年來文化一直在不斷發展和上升,直到現在。薛華則認爲現代文化中絕大部分都是悖逆神的,並且正在消亡,逐漸喪失任何做出超驗判斷或主張真理的能力。他認爲不斷抬頭的人文主義是對基督信仰的直接挑戰。我當時意識到,克拉克爵士也是這麼認爲的,然而克拉克卻把新興人文主義看作是把人從古老且頑固的宗教信仰中解放出來的思潮。令我懊惱的是,我沒有意識到克拉克文明敘事背後的預設立場。
我在高三的第一週,從頭到尾讀了《前車可鑑》。根據我13歲時開始記的讀書記錄,這是我用自己的錢買的第80本書。價格是12.95美元,當時看來是花了不少錢。我知道它值這個價,但薛華的書一開始讓我感到困擾。誰的西方文明主線敘事是對的?薛華還是克拉克爵士?當我第一次讀這本書的時候,我並不確定。克拉克爵士指出,幾百年來文化一直在不斷發展和上升,直到現在。薛華則認爲現代文化中絕大部分都是悖逆神的,並且正在消亡,逐漸喪失任何做出超驗判斷或主張真理的能力。他認爲不斷抬頭的人文主義是對基督信仰的直接挑戰。我當時意識到,克拉克爵士也是這麼認爲的,然而克拉克卻把新興人文主義看作是把人從古老且頑固的宗教信仰中解放出來的思潮。令我懊惱的是,我沒有意識到克拉克文明敘事背後的預設立場。
在我第一次讀《前車可鑑》的時候,這本書所呈現的克拉克和薛華之間的碰撞,讓我認識到世界觀大碰撞背後的原因,而這種碰撞成爲我後來生活的核心興趣和動力。一方面,我爲自己沒有認識到克拉克爵士敘事的預設立場而感到尷尬。另一方面,我知道我迫切地想了解思想、道德、藝術、文化、建築、音樂、科學、哲學和合乎聖經的基督教之間有何種交集。
薛華並沒有完美地講述我所關心的那些問題。他的一些概括過於寬泛,一些關鍵的細節卻有缺失。後世有一些評論家認爲,薛華設計了一種不可持續的努力,這種努力的目的是要藉著恢復宗教改革神學和聖經權威得以重建福音派基督教。而自由派批評者則認爲,薛華走進了一個死衚衕,福音派至今仍未從裡面走出來。
我認爲事實與這些評價都大相徑庭。後世的福音派學者在學術上的成就和在學界許多學科的影響力上,都遠遠超過了薛華。但早在現代福音派學術得著振興之前,薛華就已經在提出和回答最迫切的問題了。
在「世界觀」和「真理性命題」("truth claims")這樣的詞進入福音派常用詞彙之前多年,薛華就已經開始向我們介紹這些術語,並強調它們的重要性。他知道世界觀的大碰撞正在進行中,他非常關心當時正在基督教和知識革命之間做決定的那一代年輕人。
薛華還認爲,我們的世界觀不可避免地決定了我們對現實的道德判斷和理解。當他向克拉克爵士提出文明敘事的挑戰時,他是對的——即使克拉克爵士可能幾乎不關心薛華是個什麼樣的人。薛華並不是要讓克拉克爵士相信他對西方文明的發展軌跡論述是錯誤的,薛華更希望基督徒明白什麼是迫在眉睫的挑戰。
薛華在《前車可鑑》這本書的開頭說了這樣一句話:「從歷史到文化,這是一條河流。」他說的很對,有這樣一種流動,基督徒需要更好地知道文化在往哪個方向流動。
薛華還寫道:「人人都有預設,他們會在這些預設的基礎上持續地生活,甚至連他們自己都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有預設。」當大多數福音派基督徒還沒有意識到世界觀的風暴即將到來時,他就說這樣的話。他認爲,不斷發展的人文主義和世俗世界觀的預設首先在藝術和高階文化中顯現出來。他的觀察很對。當大多數福音派基督徒在看《荒野鏢客》(Gunsmoke)、帶著孩子去新開的迪士尼樂園時,薛華卻在傾聽和觀察,因爲一種新的世界觀正在佔領更大的文化。
薛華的正確之處還在於他觀察到個人和平和對富裕的追求是福音派信仰的最大威脅。他預言性地批評了基督教種族主義和濫用富裕的問題。當他看到像「羅訴韋德案」這樣的發展時,他的觀察也很對,他知道文化中的一些地震只是表明了已經發生的變化,更大的衝擊還沒有到來。
他提出的問題也是正確的。我們該如何生活呢?這問題在1976年曾讓薛華如此困擾,現在也困擾著我們所有人。我們即將發現,這一代的基督徒是否能信靠並活出真正的、合乎聖經的基督教信仰。我們現在該如何生活呢?
譯:DeepL;校:JFX。原文題爲"Francis Schaeffer's 'How Should We Then Live?'—40 Years Later",載於《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校刊》,福音聯盟蒙允轉載。薛華的《前車可鑑》簡體中文譯本(有刪節)由華夏出版社出版,完整的繁體中文譯本由香港宣道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