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本月(2020年10月),路易斯(C. S. Lewis)膾炙人口的著作《獅子、女巫和衣櫥》(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已經出版整整70年了。基督徒們,不妨問問自己,《納尼亞傳奇》是否能爲下一代將要面對的問題提供解決之道。我們的想像中仍然給納尼亞一席之地,那是因爲路易斯的確了解我們這些人類,雖然我們自己都常常忘記一些重要的關於自己的特性。我們不是單純的神經網絡,也不是僅僅一套肢體系統而已,我們是爲尋找路標而生的生物。因此,福音不僅用邏輯理性、實踐智慧或給自己帶來多少利益來回答我們的問題,而且——比所有這些更深層的是——用一種想像力來回答我們的問題,這種想像力能夠讓我們感受到什麼是在獅子的吼聲中顫抖。
在一項調查中,當被問及對自己最有影響力的基督教護教學書籍時,西方世界的人們——無論年齡或背景如何——幾乎總是會把《返璞歸真》列在榜單的首位或者前三。這裡麵包括了那些不贊同書中論點的人,也包括了贊同它部分或全部論點的人。對於我們這些被《返璞歸真》塑造的人來說,這本書最重要的不是關於神的那些論述——儘管那些論述是正確的,而是這本書經受住了批評者的考驗。要知道,這些批評者對待這本書就像遊戲裡的老鷹對付小孩一樣。
對許多人來說,《返璞歸真》之所以能引起共鳴,是因爲作者在書中呈現的方式。與現代宗教的玩世不恭不同,作者的語氣並不是要向我們推銷一種政治議程或一系列產品,而是簡單地、手拿菸斗爲一些真實的東西作證,或者說爲一個自己就是真理的人作證。從這個意義上說,路易斯在說服懷疑論者或安撫搖擺不定的基督徒方面最重要的貢獻,首先不是來自於他作爲牛津古典主義者的訓練,而是來自於他引導孩子們穿過一間空空蕩蕩的房間、經過一根燈柱,然後進入凱爾·帕拉維爾和更遠地方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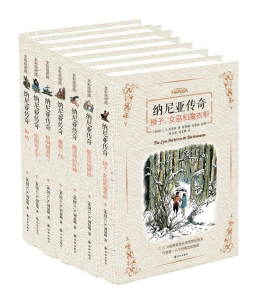 尼爾·蓋曼(Neil Gaiman)也許是當今在世的最受尊敬的奇幻作家,他不是基督徒,但他卻是前面所說的對路易斯印象深刻的人之一。他坦言在得知路易斯的「隱祕身份」(他居然是個正統的基督徒!)後感到震驚,同時,也承認自己對路易斯的魔幻世界的虧欠。「對我來說,納尼亞系列的奇怪之處在於,大多數情況下它們似乎是真實的,」他寫道。「這些都是來自一個真實地方的報告。」
尼爾·蓋曼(Neil Gaiman)也許是當今在世的最受尊敬的奇幻作家,他不是基督徒,但他卻是前面所說的對路易斯印象深刻的人之一。他坦言在得知路易斯的「隱祕身份」(他居然是個正統的基督徒!)後感到震驚,同時,也承認自己對路易斯的魔幻世界的虧欠。「對我來說,納尼亞系列的奇怪之處在於,大多數情況下它們似乎是真實的,」他寫道。「這些都是來自一個真實地方的報告。」
納尼亞這個「地方」其實頗有爭議,甚至對那些最熟悉奇幻文學的人而言也是如此,或者說對他們來說更是如此。就連路易斯的同僚因克林(Inklings)也知道,與托爾金的「中土世界」這樣精心構築的虛擬世界相比,納尼亞從露西走進衣櫃的那一刻起就顯得比較混亂。在納尼亞的世界裡,猶太-基督教的宇宙觀與希臘、羅馬和北歐神話同臺演出,而且還不止於此——連聖誕老人都出現了。
然而,《納尼亞》不僅在流行文化中堅持了70年,而且它往往陪伴了那些熱愛它的人一生之久。也許這並不是因爲人們忽視了那些看似混亂和滑稽的神話故事,而恰恰是因爲它們。畢竟,在這個宇宙中,我們已經看到時間和空間是相對的,光既可以是粒子也可以是波,構成宇宙的大部分也許是我們根本無法想像的「暗物質」,我們能說我們所知道的「真實的地方」是前後一致和可預測的嗎?我們居住的宇宙其實也很奇怪。
納尼亞的陌生性——一種被茶和壁爐等熟悉的事物所包圍的陌生性——是它今天仍然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不管是自由派還是福音派,大部分基督教護教學的進路要麼是通過學術理性主義,要麼是通過文明論證,要麼是通過左派、右派或中間派的政治意識形態。但這些都不是納尼亞的進路。
路易斯認識到,他那一代人接受福音的一個主要障礙,並不是福音對他們來說太神祕,而是太熟悉了。對現代人來說,猶大的獅子似乎很平淡,聖經的敘述與受人尊敬的文化典籍混爲一談。人們已經完全沒有辦法把福音的「好消息」(good news)當作「消息」(news)了!
「但是,假設把所有這些東西投進一個想像的世界,去掉主日學加給它們的彩繪玻璃,就可以使它們第一次具有真實的效力,」路易斯寫道。「這樣能不能越過那些警惕的惡龍呢?我認爲可以。」
這就是爲什麼對我們許多人來說,當我們走近鬃毛暗淡、死在石桌上的阿斯蘭時,淚水會湧出,不管我們讀了多少遍。這就是爲什麼,無論我們有多麼厭惡那個討厭的埃德蒙,我們偷偷地在內心裡仍然會覺得自己和他是一類人。這就是爲什麼,當我們讀到阿斯蘭講到埃德蒙的時候說:「這是你的弟兄,不要再談論他過去做過什麼了!」的時候,被這種恩典打動。這就是爲什麼,當人們深陷失望、哪怕在臨終的時候,聽到「阿斯蘭在行動,女巫的魔力正在減弱」這句話仍能心生盼望。
路易斯認識到了聖經中關於人性的核心真理。我們會保護我們的良心,我們會塑造我們的直覺,我們還會「扭轉」我們的理智(就像我們看新聞的時候一樣)過濾掉任何不符合我們自我形像的東西。但是,只要走出自己的心所建立的牢籠,恩典的喜樂就會令我們感到驚訝。先知拿單對大衛講了小羊羔的故事,因爲他不只是想跟大衛講道理,而是想讓他在情感上參與到一個國王看不到這是關於他自己的故事中。當然,耶穌用故事、圖像和比喻向我們說話,並不是爲了讓我們能夠抓住裡面的命題或者把它們歸結爲道德上的應用,而是因爲「一個人有兩個兒子」比「饒恕是好的」更能在靈魂層面上直擊我們內心。保羅也是如此,他並不是簡單地說:「神與以色列的約仍然有效」,而是說:「你是從那天生的野橄欖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性得接在好橄欖上,何況這本樹的枝子,要接在本樹上呢!」
《納尼亞傳奇》之所以經久不衰,不是因爲對其中寓意的解讀,例如「石桌」就是十字架,「白女巫」就是魔鬼,《魔法師的外甥》就是《創世記》等等,而是因爲它們把我們帶到了意想不到的地方,讓我們重新操練感受真實的事物,就像我們第一次感受它們一樣。而這些故事之所以持續存在,是因爲它們有耐心等待,就像一粒種子落在冬日的土地上,等待我們心靈的積雪開始融化,等待聖靈的風吹到他想去的地方。在這個世俗化的時代,這不失爲一個好的開始。
當然,這個70年前的項目並不是我們的全部。就像教授告訴孩子們,那個空房間不是他們可以隨意控制的門戶:「你們不能通過這條通道進入納尼亞。」他說,「事實上,不要想著怎麼去那裡,通往納尼亞的通道會在你不注意的時候來臨。」不過,70歲是一個美好的長壽年齡——這是《聖經》告訴我們的。我們應該反思一下,我們從路易斯這個講故事的人身上學到了什麼,我們可以學習一個能抓住想像力的福音呈現方式。而我們也可以「再往上走,再往裡走」,成爲《魔鬼家書》世界裡的納尼亞基督徒。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Still Grips Our Imagination, 70 Years Later